阅读:0
听报道

“文化大革命”噩梦醒来,如何总结“带血的教训”(邓颖超语),避免这场党内外一致认定的“十年浩劫”再次发生,作家与老一代革命家一道,陷入的沉痛的思考。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写了一个在“造反有理”年代学坏的男生宋宝琦,这个不学无术的小流氓重回班级,引发女同学集体罢课抗议;但他用更犀利的笔触,勾勒出一个貌似政治进步却又精神扭曲的团支书谢惠敏,让那个年代的读者深为震惊。
谢慧敏应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但她对《牛虻》这类写男女、写外国的“资产阶级书籍”深恶痛绝;发现同学在自习课上偷看小说《青春之歌》,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立刻没收上缴老师。她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几乎没有业余爱好,却高度警觉地关注班上同学的思想动态,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
谢慧敏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品质,例如不辞辛苦,坚持把同学随手带出的一棵麦穗送回村里,因为不能让贫下中农受损失。只是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扭曲了本该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天真烂漫。谢惠敏给老师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老师没有责难那两个不像样子的团员,却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那一天热得像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问她:“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简直不能理解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而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当过15年中学教师的刘心武,揭示了极左政治给年轻一代带来的精神创伤。在刘心武看来,谢慧敏和宋宝琦同属问题学生,只不过两人的伤痕“一暗一明”,“一深一浅”。“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残害了多少青少年纯洁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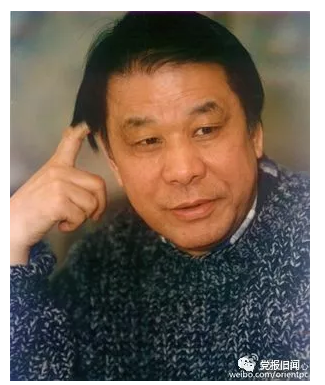
《人民文学》编辑部被这部小说极大地触动了,却又鼓励重重。一派意见认为,小说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主编张光年闻讯召集有关编辑开会讨论,这位当年《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提出:小说题材抓得好,不要怕尖锐,但要准确;小说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却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张光年的意见转达给刘心武,刘对作品进行了局部修改。《班主任》顺利发表在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比卢新华1978年发表在《文汇报》的小说《伤痕》还早,可以视为“文革”后“解冻文学”的开山之作。一石激起千重浪,小说风靡一时,杂志社收到的读者来信之多,办公室书柜容纳不下,不得不去买麻袋来装。
这是一个时代的觉醒。“这部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勇气和敏锐的眼光,正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民族性劫难,看到这场劫难不仅造成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扫荡性的摧残,而且造成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严重扭曲。谢惠敏式的人物就是被扭曲的典型。新时期文学一问世,就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观念产生巨大怀疑,就热切地关心着人,呼唤着对人的尊重。这些文学的拓荒者凭着作家的直觉,感悟到过去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是非人道的。新时期文学的深刻性正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当时一批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小说,都是作家用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眼光所看到的伤痕与泪痕,都是对‘文化大革命’那种非人的悲剧的揭示。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最富有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人民日报1986年9月8日《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
如果谢慧敏的班主任在今天,敢于纠正学生被极左观念迷惑的偏执和无知,会不会惹出麻烦而被下岗?当年虽然有人指责《班主任》这样的作品负能量,但主流舆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人民日报 1979年8月20日刊出杜雨的文章《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为什么对这类短篇小说的非议声最近也大大提高了呢?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这类作品近半年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人民内部、甚至我们党内的一些问题。大概正是这一点使有些同志不能容忍,认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和人民。文章严正指出:
今天,我国人民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痛定思痛,正在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还需要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当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非常严峻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对林彪、“四人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探索和剖析。由于这伙敌人是我们党内生出的恶性瘤,我们在剖析的时候必然会接触到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必然会触及到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相反地,我们倒想问问那些持非议的同志:当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这样做的时候,难道不正体现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不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鲜明党性吗?
如果说刘心武揭露了谢慧敏身上“文革”的“内伤”,作家铁凝则塑造了一个改革年代人性和个性开始复苏的女生形象。从“文革”开始后“铁姑娘”的遍地开花,中国社会步入到病态和灾难的深渊;而新时期之初,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拐点,到铁凝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中,安然坦然穿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拒绝造作虚伪,表明“女性逐渐走出‘非女性化’的年代,中国社会又开始恢复正常。(人民日报2010年9月21日《如何写好一个“女”字》)
文章原载于“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2018年9月29日)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